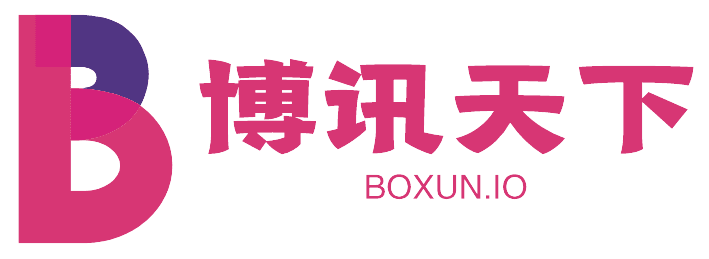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— 在美国女足国家队在 “SheBelieves杯 “上抗议她们的联合会三年后,加拿大的球员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情况。
尽管两队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竞争,但在场外为公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也存在着友情。
周四,这将在球场上为全球观众上演。
美国前锋梅根-拉皮诺周三说:”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,显然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,在场外做所有这些事情并必须进行表演是多么困难。”在两队计划在表演赛上进行比赛的前一天。
加拿大球员上周以罢工威胁他们的联合会,因为他们说与男队相比,条件和资源都不平等。球员们还说,他们在2022年根本就没有得到报酬。
加拿大足球协会的回应是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,如果球员不参加SheBelieves杯,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的个人损失。
加拿大球员表示,他们将参加这次比赛以示抗议,当他们周四在Exploria体育场上场时,他们将以某种视觉方式表示。美国队长Becky Sauerbrunn说,她的球队将加入他们。
“我认为你应该计划在明天的比赛中看到一些东西,”绍尔布伦告诉平博。”无论是声明还是场上抗议,我想都会有我们组织的东西,我们完全支持他们。”
周三,加拿大球员在Exploria体育场进行了训练,他们穿着没有标志的装备和从内向外翻开的服装,以隐藏加拿大足球的标志。
这并不是美国足球每年举办的友谊赛SheBelieves Cup第一次陷入女子比赛的劳资纠纷中。
2020年,美国女足将她们的热身衣从内向外翻开,以隐藏美国足球的标志,只显示联合会徽章的轮廓和上面的四颗星,代表她们赢得的四个世界杯冠军。
抗议是为了回应几天前的法律文件,其中美国足球队的律师作为多年来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的一部分,认为女性是低等运动员。
球员们和美国足球队最终在去年结束了他们的斗争,达成了2400万美元的补偿协议和新的集体谈判协议,为美国男队带来了公平的薪酬。
美国男足和女足将平分他们的世界杯集体奖金,这是六年斗争中的最大障碍之一。
周四,美国老将拉皮诺、绍尔布伦和亚历克斯-摩根表示,他们将向加拿大同事提供任何建议。绍尔布伦已经与加拿大队长克里斯蒂娜-辛克莱尔进行了直接联系,辛克莱尔是她在波特兰桑斯俱乐部的队友。
加拿大是美国国家队最常见的历史对手,也可以说是它最大的对手,但两个项目之间的交集是非常大的。
大多数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历史上都参加过全国女子足球联赛,加拿大的许多顶级球员都在美国大学系统中踢球。
“只是有些事情比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大得多,只是基本的人权和尊重,以及获得他们应得的东西,”拉皮诺说。”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奥运冠军,所以那是当之无愧的,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
拉皮诺补充说,她感到困惑的是,为什么加拿大足协在赢得一个重要的国际冠军后,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其球员。
2021年,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在东京奥运会半决赛中击败美国队,赢得了该国的第一枚奥运足球金牌。这是在2012年和2016年连续获得奥运会铜牌之后。
去年,加拿大男队36年来首次进入世界杯,在比赛中的工作人员比女队通常得到的多一倍,加拿大女队前锋珍妮-贝基本周说。
贝基当时在卡塔尔,亲眼目睹了男队的设置,因为加拿大未能从小组赛中晋级。
周二,Beckie说,这支加拿大女队可以用世界杯冠军来延续这种表现,但他们需要联合会提供更好的支持,包括增加人员配置和更多的球员参加训练营。与此同时,加拿大足球协会正在计划削减预算。
贝基和她的队友们还说,他们希望看到进一步投资于妇女的青年计划,以便该计划的成功能够长期维持下去。
至少,加拿大球员说,他们希望从2022年起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,否则他们将不会在4月比赛,这是今年夏天世界杯期间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国际足联官方窗口。
“我不打算撒谎,这很紧张,”辛克莱尔说。”我在这支球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,而且一直在与CSA进行不断的斗争,试图提出进步的CBA。作为男子和女子[球队],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,必须有所改变。”
周四的对手为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,同时也是他们斗争中的坚定盟友。美国球员多年来表示,他们的同工同酬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。正如Sauerbrunn在周三所说,美国人在这场斗争中 “写了剧本”。
最近,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的球员和球队都在进行类似的斗争。
拉皮诺说,她认为为公平而进行的场外斗争激发了球员的表现,至少在她丰富的经验中是如此。她作为赛事的最佳球员赢得了2019年世界杯金球奖,同时还在社交媒体上领导了一场针对当时美国总统唐纳德-特朗普的斗争。
“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,无论是英格兰队以这样的方式赢得欧洲杯,还是WNBA和他们的新CBA,还是冰球队,还是我们的球队,NWSL,加拿大现在,”拉皮诺说。”我们在场外都是同一个团队,所以这一切感觉就像一个雪球效应。我意识到我们的团队是最早这样做的团队之一,是最响亮的团队之一,也是在球场内外最成功的团队之一。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。
“我们希望它发展得更快,球队不必这样做,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越来越容易,而联合会和组织拒绝某种基本就业权利和基本人权则要困难得多。”